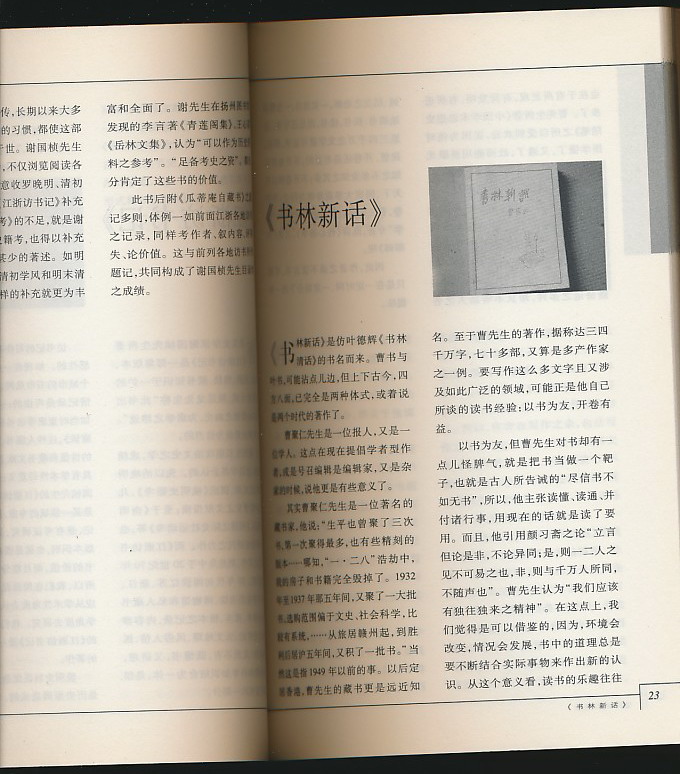作为小说家的李少君
写在前面:
夜谈君这篇旧文写得较少,在2006年。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李少君是诗人、评论家和编辑,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却较少为人所知。1996年到2000年左右,建省不久的海南岛陷入某种低潮的时候,他曾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他在《1999年的A城》这小说的题记里写道:“我忧郁的时候就想写小说。”
李少君小说集《蓝吧》
一
看的第一篇李少君的小说是《蓝吧》,在1996年的《天涯》杂志上,那本《天涯》的封面是蓝色的,很光滑,和后来的牛皮纸封面的简约高雅不可同日而言,依然隐约可从那里看出那个时代的浮华与浮躁。《蓝吧》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出现,正好是一种时代的暗合。李少君的小说集《蓝吧》出版已经是2006年初了,这之间已经过了十年,十年已经足够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人生的态度。
据说1988年之后的好几年中,海口是一个让人狂欢的地方,可惜我晚生了好几年,在他们那代人疯狂挥洒自己的青春的时候,我只能从他们的书中找到我想要了解的曾经离我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的疯狂与浮躁,也许我正在走着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而不自知。曾经在一本叫做《海口过客》的小说中,曾经在潘军的《海口日记》中,我看到了那时这个海岛上发生过的美丽与丑陋。现在,又在李少君的小说集《蓝吧》中,我再次印证了那些间接记忆,好像我也曾经经历过那个疯狂的时代。
洪治纲在评论李少君小说的时候,把他的创作归结为“感伤的救赎”。李少君也多次强调自己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感伤,他说过:“无论面对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我的反应只有两个:我伤感,我痛。”李少君在自己平静的叙述中,感伤和不安的情绪始终在贯穿,可若是纠根揭底的寻找,我们或许能找出这种感伤来源于对时代变幻的不安与对人生的虚妄,这是每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但各人在处理的时候却有不同的方法。李少君在小说《1999年的A城》中有一句题记:我忧郁的时候就想写小说。
“单个的人难得疯狂,疯狂出现在群体、社团和国家里”,李少君的很多小说都在反映着一个疯狂时代那难为外人道的隐痛。《蓝吧》中的我和蓝吧的主人蓝林,《海口之恋》中千里南下的林君,《废墟》中阳痿了的杨晨,《说不定什么时候出错》中的西林,《人生太美好》中的顾扬……每个人都在不能把握的现实面前精神漂流,个人的力量在不能把握的潮流中,显得可笑而可怜。
《蓝吧》中,“我”是这么样一个人“小白脸,穿得挺时髦,两眼无神,满不在乎地迎接你的目光”“我失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差不多要折腾到凌晨天快亮时,才能闭一会儿眼睛。我才二十多岁,却夜夜失眠,这是我当时唯一的苦恼。”苦恼中的“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地方:蓝吧。这个家庭好却没有生活目标的“我”喜欢上了蓝吧,在蓝林的鼓励下,“我”办花店的念头大起,最后却因为母亲的一句话,所有的热情消失殆尽。依旧是整日的晃悠,在和蓝林一起看到一胖一瘦两个人在蓝吧里面殴打一个不肯过来陪酒的女孩后,心中怒却不敢言,终于是当了长脖子的看客。在那个时代和人都一样疯狂的时候,握紧的拳头最后也总要松开,笙歌不灭的地方,映照出了可怜猥琐的影子。
《海口之恋》故事很简单,简单到可以只当爱情小说来解读,但若只把这小说看成爱情的记述,我们就忽略掉了很多背后的东西。大学毕业后林君在长沙的一个机关单位上班,在收到老同学刘义和大学里曾经交往过的女生于晴在海南给他的信后,对特区有了一份向往,他带着激情到海南,希望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找到激情和爱情,最后却发现往日的故人却早在物欲横流的地方也迷失了方向,他落荒而逃回到长沙,心灰意冷之下随便找了本单位一个女孩结了婚,断绝了和特区的联系。
《废墟》中,杨晨在结婚前因为妻子好朋友刘露暧昧的一掐,这短短的一瞬,让杨晨遐思无限,曾经对性生活需求无度的杨晨好像忽然变成了阳痿。“当杨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过了好几个月了,杨晨和丽丽好几个月没有做爱了,而且,更要命的是,两个人似乎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后来在刘露到他家的时候,杨晨压制不住要和刘露发生关系,刘露落荒而逃。之后一个让杨晨心动的明星出现,杨晨依然未能恢复性能力,有一天他却在妻子工作的地方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做爱。
《说不定什么时候出错》中,李少君用了两条线索的复调形式来叙述,但无论是西林和余虹、杨青几人的纠缠不清的感情纠葛还是罗强、刘国民、梁珠几人利益纠缠,偶然出现的杨青,失踪不见的刘国民,带动了整个故事的向前,没有人在最后是赢家,所有人都在不能把握的环境中迷失本性,最后失去了一切。
……
我们没有必要把每篇小说都来分析一下,却也可以看到李少君的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们在淡然的叙述中,承受着多大的灵魂负重,在现实得那么现实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渺小而无力。我不清楚李少君是有意或者无意,他的语言始终都是淡淡的,用对话,用人物不经意的表情,透露出每个人都密而不露的心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我的艺术生活》最后一章中说:“人必须与敌人作斗争。我们的新角色不如我们以前所担当的老角色那样动人。但是每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界限。我并不抱怨。”李少君小说中每个人都有着纠缠不清的宿命般的感伤无奈,这并非只是由于环境与人生的不可把握,更加是由于每个人不甘心被环境把握而希望去改变自己所处的境地,希望自己的努力会给自己带来幸福。若是真的甘心接受了,宿命感也不会那么强烈,在我们每个人都碰得头破血流后,我们才更知道石头的硬和伤口的疼。
《蓝吧》发表于1996年第四期《天涯》
二
孔见在《种瓜得豆——关于1988年的海南岛的我的零碎的回忆》中说:“机会似乎到处都有,但它转瞬即逝。人们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心事重重又魂不守舍,走在路上眼睛注视着远方。我的一个同事在横穿马路时被撞得头破血流,但是,直到爬起来,他都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把他撞了。”李少君则在自己的文章《何谓感性生活——以海口为例》中把1988年那件事称为“‘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青春大放纵”。他说:“爆发过后是长久的极端的散漫与颓废,甚至有一点堕落的因子。”就是这么一个欲望疯狂成长的时代,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等到事过境迁之后,回头看去,这个时代的疯狂已经在我们的疯狂中变态了。改变是不可能的,能做的也不过是把这些事情记下来而已。
“爱的呻吟和垂死的呻吟是何等相似”,李少君小说中的人在呻吟时候谁能分辨那是爱的呻吟或是死亡的呻吟?何况这两者本就没有多大的区别。在整个时代狂欢的时候,作为个人,想要在这欢呼声中保持自己的安静的一隅无疑痴人说梦,网络中曾经流传一句话是: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在这欢呼喧闹中,谁会在乎个体的隐痛?
我们回头过来看小说。《蓝吧》中,“我”在整个特区建设热火朝天的时,却是一个悠闲的浪荡子,他看似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看着这场动荡不安的变革,可其实他也身在其中不能自拔。《1999年的A城》中,李少君试图用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展示一个城市繁华背后的糜烂。我查了一下小说后面的附表,这居然是发表于1995年《椰城》上面的小说。于是可以想象,所谓1999年世纪末A城的城市万象只不过是海口某个年代的缩影。小说中,高和卖衣服的小姐在帝豪商业大厦九楼的初次见面就在更衣室引发欲望的战火,黄小姐,红小姐,章老板,长发诗人,所有的城市边沿人物纷纷登场,在这个叫做A城的地方尽享繁华,最后死的死,抓的抓,而“1999年A城的这种浮华气息不知还将延续多久。”《无事生非》中,莫林泡上王虹甩不了手,居然设计让自己的朋友阿亮在王虹醉晕的时候进房间,他自己再进去,狠抽王虹一耳光后说:“你干的好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出错》中,各色人物更是用尽机关,在欲望下不辨方向,人的感情在其中居然是那么脆弱虚假。
每个人都受到伤害,没人得到救赎,所有人都输了青春,那赢家是谁?李少君从来不掩饰自己对诗人多多那首《青春》的喜爱甚至是偏爱,这只是因为诗中这么几句:“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们大多都是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正因为年轻,当美好失去之时才更感可惜与无奈,当青春被杀虫剂灭绝时,才让人无话可说。一个叫什么H.D.Thoreau的家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已经构造了一种命运,一个命运女神,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这话让我们感到绝望,但当事实真的曾经这么绝望过,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挽救?
三
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种记忆,也不可能只有关于某件事情的记忆。经济特区海南有对李少君很重要的记忆,却绝非他唯一的记忆,我尝试去找他的心底的别处时,发现了两篇在小说集中很不一样的篇章,一篇是《梦醒此时》,一篇是《酒中岁月》。
《梦醒此时》发在1991年的《天涯》,《酒中岁月》却是2003年发在《安徽文学》的作品,这么把相隔时间列出来,方便我们对着两个小说解读。《梦醒此时》写了一段从高中到大学的爱情,夹杂着主人公一直做的一个梦。“每天,我在梦中尽情地哭泣,放肆地哭泣,但醒来时,脸上泪渍皆无。”姗姗的死,让主人公在大学里面行为疯狂又清高自傲,美好青春的破灭加上早已苍老的旧梦,感伤不已。
《酒中岁月》的结尾是吓我一跳的。一群临近毕业的大学生,终日烦恼在毕业分配的事情上,只得借酒消愁经常寻醉,一直被当成第一主人公描写的梁云始终是有想法的人,最后却因为分配问题用和姗姗虚假的爱情通过关系,得到了本该是他好朋友的分配名额。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着各个人各次喝酒中似乎可以忽略的谈话,而结尾猛然的转折,前面的描述忽然就让人伤感起来,一直无意识中埋下的伏笔,所谓的青春,在利益面前,居然破碎得那么快那么直接那么快速。
“只有人能抵抗地心引力的方向:他在向上堕落”,在没有特区灯红酒绿的诱惑下,依然有着别的诱惑在引诱着李少君小说中的人物,在向上爬的借口下,一切堕落,一切和地心引力相反的堕落来得这么让人感伤而无望。
四
洪治纲说到李少君小说,把他小说中的人物归结为一种感伤的救赎,一种沉沦之后的自我复原。我们若只是在这自己造成的感伤和无奈中不可自拔,那人生就真的无望了。更多是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而不是小说写作者的李少君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对“上升的鸟减轻了我们灵魂的负担”这句诗的喜欢。他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诗歌能让人灵魂减压,小说让人对生活绝望。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已经足够颓废糜烂了,而很多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居然比我们还要颓废糜烂,这真他妈的绝望。
自称“我忧郁的时候就想写小说”的李少君若一味在自己营造的小说氛围中沉迷,也不会是一个让上升的鸟减轻灵魂负担的人。《蓝吧》中的“我”和蓝林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生太美好》的结尾:“‘人生太美好’顾扬喃喃地念了一遍。飞机一阵呼啸,腾空而起。”有了飞翔的结尾总比沉没要好。《西安未眠夜》中放纵的感情成了灵魂的归属。《海口之恋》中的林君或许真对特区绝望了,但回到原先的单位过平稳日子难免也是他最好的归宿……
爱米莉•狄金森说过:希望是种长羽毛的东西。这是否说明希望和上升的鸟一样,可以飞高,减轻我们灵魂的负担。伍迪•艾伦则说:永远的虚无没什么所谓,如果你为之穿着适当的话。这好像让我们觉得,其实无论希望是否能减压,若真的当成没所谓了,好像一切就好办得多,可若都如说的这么简单,我们也不会有那多的纠缠与无望。
在经济大潮中,社会大潮中,我们既然都无法把握一切的方向和人生,能够保持心底一丝的准则已经是不容易了。近年来对诗歌有着更大关注的李少君心底自有不能改变的准则,他活在物欲横流的特区却并不为物欲所左右,我曾经在网上找过别人关于李少君的记忆,看到了下面一段颇带暖意的记录,作者是谁我没有找出来,也没有找出来的必要:
“湘乡李少君,现为《天涯》杂志社主编。
“约在1989年下海南,比其他湖南文化人早一步立定脚跟。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尤其小平同志南巡后,全国掀起新一轮南下狂潮。不少湖南文化人洪水一样往南冲,席卷广东、海南。
“这股泥沙俱下、鱼龙俱下的狂潮中,很多人都满怀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英勇。
“结果很多人在或妖魔化或神圣化的大风车前,头破血流,晕头转向,以致在广东、海南茫茫南方璀璨星空下,竟无一可立足之地,更有身份证等各类证件丢失者,种种狼狈情形,不可一一名状。
“李少君因先下海南,早已立定脚跟,在此非常时期,乃空出一屋,专供湖南或武汉大学校友各落难朋友居住,甚至供以饭食。
“曾在饭桌上听昔日落难者,讲起李少君的义气。称,此举可誉为“一饭之恩”,虽“涌泉难报。”故李少君在湖南颇多真正的铁哥们。
“今日,与长沙里手同饮于东风路“大碗厨”(长沙一餐馆),里手召来他的同事朋友李舟军教授,此人即为李少君之兄。偶亦稍稍谈及此事。问,当时李少君“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可他自己住在哪里,是否家人啧有怨言。
“李舟军答,我弟住在他岳母娘家。自己的房子内开四五张床,专供朋友们休养生息自由出入。亦与前言相映证也。”
在这里大段引用别人的文字,好像已经脱离了小说谈人物,可按照传统的说法,或许《蓝吧》中整天逛悠的“我”是李少君的另外一面,蓝吧的主人或许也是另外一个李少君;《海口之恋》中的千里南下的林君是不是也是当初带着梦幻南来又曾破碎的李少君呢?李少君在自己的文章中这么回忆:“1993年的高潮之后是急转直下的滑坡,我刚刚亢奋起来的心绪随即跌入失望的低谷。”这些他们那代人大都经历过的事情在他小说中,可李少君却走着和他笔下的人物不一样的道路。他在自私横行的时候,可以慷慨仗义,在环境无奈时候做出了能够作出的反抗。于是心底保存诗意的李少君在经历理想破灭后依然能够站起来,而一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下了。
五
每个人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心事,别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那身在其中人的想法。很多不为外人道的隐痛或许不只是一个狂欢的时代造成的,因为在一个狂欢的时代,有人哭着自然也有人笑,从开始到最后,总有一些该死该倒下却一直没死没倒下而比任何人活得都惬意。在一个狂欢的时代,许多人希望破灭了,更多的人在别人的破灭之中狂欢。
多少人在这场失去理智的狂欢中能保持一点自省?
李少君在小说中表达的不只是关于一个迷乱时代的记忆,又或许他一点都没有表达这个的意思,一切被我强加进去的解读只是我为了试图了解那个时代被我生硬的想象出来的,那只是我的误读。前面说过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说过前面那句话后,接着的句子是:“我只是叙述事实。抱怨在我们看来是罪恶。我们曾经生活过。我们更应该感谢上帝,容许我们用眼睛望见未来的蒙?景象,望见我们身后将出现的世界。”
试图从小说中看清楚一个时代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幻想,作品不是生活的复制,即便复制也已经不是原品,亲身经过的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经过了什么,正在经历着的我们也无法说出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所谓的《海口过客》、《海口日记》、《蓝吧》、或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没有冬天的海岛》都只是一些人零星不完整的回忆,把这当成那个时代的全部,自然只能看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变形。
近来更多从事《天涯》编辑和诗歌评论、随笔写作的李少君身上更多的是理性和智性,年轻时的狂乱毕竟只是那个时代不成熟的表现,海南发展经过泡沫经济后也在稳步上升,当年那些和海南一起经历泡沫的年轻人自然也已经长大成人。李少君在《从莽汉到撒娇》中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经历了理想的破灭与激情的骤然降温,经历了商业化的彻底洗礼与改头换面。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的年纪不过增加十岁,体重却增加了几十公斤……在一般人眼里,也是社会中坚了……可是夜深人静之际,半夜梦中醒来,却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还有很多设想尚未实现,还有很多壮志未酬……”可设想未实现又如何?壮志未酬又如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已经不和当年一样了,心中不甘也只是不甘而已,能够在深夜面对自己读几行诗,已经足以让激情沉淀。
《圣经》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里有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无论时代是否狂欢,无论青春是否虚妄,无论上升的鸟是否能减轻灵魂的负担,只要在我们生活每一地存着指望,坚固而牢靠,是时代狂欢造成个人的隐痛还是个人的狂欢造成时代的隐痛,都已经不重要了。